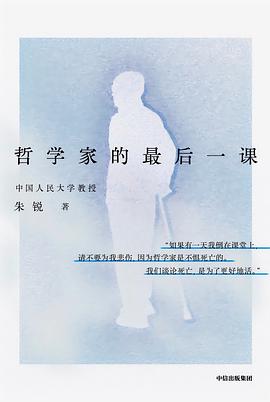【专栏】| Conlumists>陈娅杂谈
JM特约撰稿人 陈娅,武汉, 2025-04-20
援笔启思,思以致远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源自作者朱锐在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以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汇集了他在哲学研究领域 30 余年的思考。朱锐在书中将“死”(dying)与“死亡”(death)明确区分:“死”是生命体在终结前经历的痛苦过程,而“死亡”是这一过程的终点,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他提出,“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重生的可能——若万物永生,宇宙将陷入停滞的泥潭。这一观点融合了中西哲学的智慧:从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的“万物轮回”到庄子的“大化流行”,朱锐以跨文化的视角揭示了死亡的积极性。
朱锐以“化作春泥更护花”为喻,强调个体的消亡是回归自然循环的起点。他援引薛定谔的“生命为何比原子大”之问,指出生命的意义在于从无序的原子运动中提炼出有序的自我意识,而死亡则是将这种有序重新释放回宇宙的洪流。这种“小我融入大化”的生死观,既呼应了道家“一气流行”的生生哲学,也与现代科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形成对话,展现了哲学与科学的交融。
朱锐在癌症晚期的身体体验,成为其理论的具身化注解。他形容自己如“寄居蟹”,灵魂逐渐脱离衰败的躯体,而这一过程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拒绝无意义的生命延续手段,坚持清醒的意识与尊严的告别,甚至在病房中与学生探讨“恶心的悬置”现象——当爱超越生理本能,护理者与垂死者的亲密关系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以病痛为实验室的哲学实践,使抽象理论获得了血肉的温度。
朱锐批判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回避与恐惧,认为这源于对“小我”的过度执着。他提出“练习死亡”的苏格拉底式命题,倡导以“儿童式的积极恐惧”替代“成人式的消极恐惧”,即通过直面死亡来激活对生命的热爱。书中以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为例,说明恐惧的本质是对未知的屏障,而哲学的任务是拆除这些屏障,让人在有限中触摸无限。
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深化了主题:美国画家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匍匐望向远方的残疾女性,象征人类在死亡逼近时仍保持对生命的凝视;而“寄居蟹”则隐喻灵魂与肉体的逐渐分离,外壳(身体)的沉重与内核(精神)的自由形成张力。这些意象将哲学思辨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表达,让读者在情感共鸣中领悟死亡的超越性。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并非一部悲情的临终手记,而是一曲充满生命力的启蒙乐章。朱锐以“死亡是生生不息的来源”为枢纽,打通了东西方生死哲学的脉络,并通过自身的“生命实验”证明:真正的哲学家不惧死亡,因为他们已将死亡转化为理解存在的透镜。正如他在病房中对学生所言:“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这本书既是对个体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文明如何面对终极命题的深刻启示。
朱锐(1968-2024)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玉章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森林湖文理学院哲学系终身教授、神经学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横跨哲学、艺术学、神经生物学,在心灵哲学、神经美学、比较哲学、古希腊哲学等研究领域做出积极贡献。 在生命的最后一轮春夏,他带病讲课,探讨自己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广泛报道。
作者简介:陈娅,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编辑:不夜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