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不夜侯,深圳,2025-08-12
编者按:曾经,非洲草原上的象群如繁星般浩瀚——16世纪仍有约 2600 万头,而今仅剩 49 万;亚洲象更只剩不足 5 万头,连中国境内野生个体都仅 300 多头,仅为大熊猫的1/6。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World Elephant Day)。该纪念日由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帕特里夏·西姆斯(Patricia Sims)等人于2012年发起,旨在唤起全球公众对非洲象和亚洲象生存困境的关注。
大象是环境变迁的沉默见证者。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将这些体重可达数吨的巨型动物比喻成“矿工的金丝雀”——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早期预警系统。一头成年象每日需消耗150公斤以上植被,饮用近200升水,活动范围可达数百平方公里。这种生理特性使象群成为环境变化的敏感指示器——当它们开始退却,往往意味着整片森林生态系统已走向不可逆转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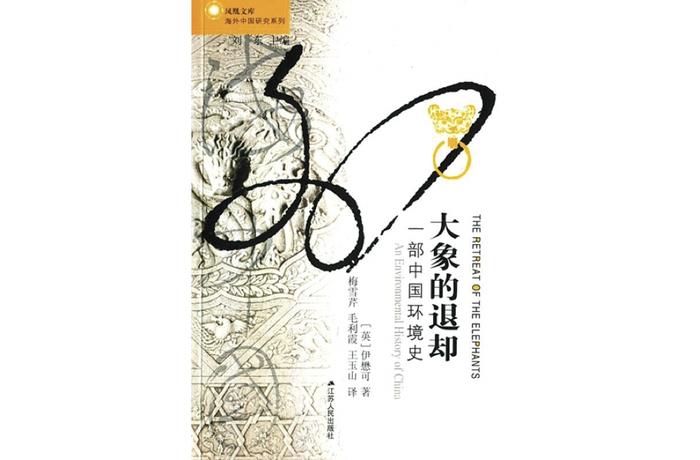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书中以这种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为线索,展开了一幅跨越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变迁图景,通过大象在中国版图上从北向南、从中心到边缘的持续退却,揭示了中国文明发展背后沉重的生态代价。
“豫”——河南这个简称的右半部分是一个“象”字,隐藏着中国环境史上的重大秘密:三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曾遍布大象的足迹。《大象的退却》通过精心绘制的分布图,展示了大象在中国版图上逐步南撤的轨迹:
- 公元前900年(西周时期):大象仍活跃于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
- 公元580年(隋朝开国):大象退至河南及江淮之间
- 公元1050年(北宋时期):分布于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 公元1450年(明朝景泰年间):仅存于福建、两广
- 鸦片战争前夕:退缩至云南一省范围
这一持续数千年的退却过程,恰如此书作者伊懋可所言:“一部中国环境史,完全可以用大象的退却路线来概括”。通过追踪大象的足迹,作者巧妙地将中国四千年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编织成一部宏大叙事。
栖息地的消亡
大象退却的首要推手是栖息地的丧失。伊懋可指出,农耕文明对森林的敌视深植于汉文化基因中——“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扩张模式,随着汉族人口增长和政治版图拓展,不断吞噬大象赖以生存的森林空间。
书中颠覆了人们对“刀耕火种”的简单认知:传统上被视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在伊懋可笔下呈现出复杂的生态智慧。他引用云南少数民族的耕作实践显示:布朗族和哈尼族的轮歇农业有着严格的伐木规范(小树擦地皮砍,大树只砍枝)、烧地流程(留防火道、分次燃烧)和轮作周期。这种耕作方式虽改变了原始森林面貌,却能与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然而当汉族移民带来持续开垦、拒绝休耕的农耕模式后,森林再生能力被彻底破坏,大象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崩塌。
水利工程的双刃剑
伊懋可最具创见的贡献在于提出“技术锁定”理论——中国古代大规模水利工程在造就农业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僵化。京杭大运河等巨型水利设施在建立初期带来显著效益,但随着时间推移,维护成本呈指数级增长,陷入“次好技术因先发优势而持续支配”的困境。
这种“锁定效应”在黄河治理中尤为明显:秦汉时期在西北部的农耕推广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河”变成了“黄河”。为应对泥沙淤积和洪水威胁,历代王朝不断加高堤坝,形成恶性循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迅速淤积同样以珠江流域森林破坏为代价。水利工程创造的短期红利,最终需以更高的生态代价偿还——这一洞见对理解当代中国水利工程仍有警示意义。
人类贪婪的掠夺
除生境破坏外,人类对象牙、象鼻的贪婪需求加速了大象的消亡。书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唐宋时期岭南地区盛行食用象鼻,“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惠州曾发生野象闯入城区事件,最终在人类围猎中演变为悲剧。
更致命的是大象极低的繁殖率——孕期长达22个月,使种群在人类猎杀压力下毫无恢复能力。当猎杀效率随武器进步而提高(如明朝军队用火器击溃战象),大象的退却便加速为崩溃性消失。
《大象的退却》写于二十年前,却精准预言了21世纪的中国生态困境。2021年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事件,戏剧性复现了书中描述的人象冲突——象群因保护区森林过度繁茂(“森林化”导致地表喜食植物减少)被迫进入农田觅食。这一事件证明:即使建立自然保护区,若忽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仍无法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
当代中国的生态挑战与历史一脉相承。三北防护林工程可视为对古代森林滥伐的补救;南水北调工程延续着水利治理的传统智慧与风险;而云南野生象生存空间的持续萎缩,恰是四千年“退却”的现代缩影。伊懋可提醒我们:生态危机不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文明发展的伴生物。
超越“退却”的未来之路
在批判之外,《大象的退却》也暗含重建共生的可能。书中对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发掘,如傣族养象耕田,对轮歇农业生态合理性的肯定,都暗示了不同于汉文化主流的发展路径。这些案例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关键启示:生态治理需超越单一的“保护vs发展”框架,寻找多元的地方性知识。
全书以一个问题作结:“大象一退再退的目的地又在哪里?”答案不在书中,而在我们手中:能否打破“技术锁定”的魔咒?能否避免内卷化的生态陷阱?能否在象群最后的栖息地构建真正的共生文明?
当2021年北迁象群在人类引导下安全南返,我们似乎看到一线希望——这一次,人类选择为大象让路而非驱赶。
编者注: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John Dutton)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编辑: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