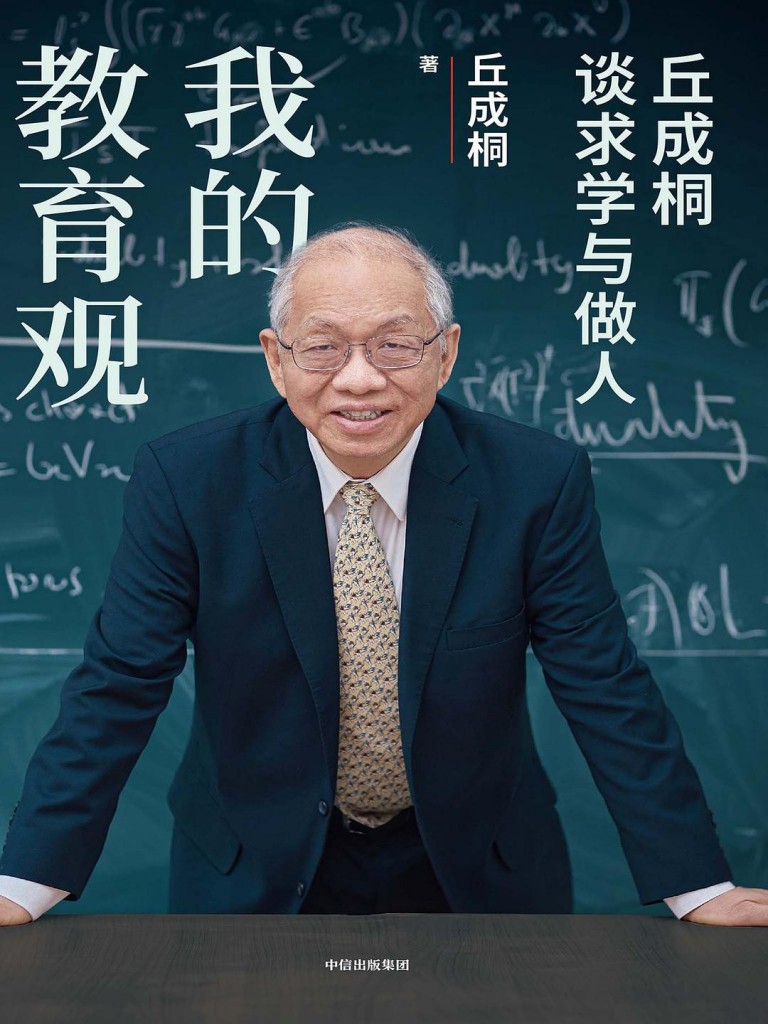作者:丘成桐
数学教育
我个人认为,教数学当然要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对数学本身的美丽的欣赏能力。但是,我们教学生,首先还是要让学生弄清楚学习数学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它绝对不是为了学习集合或者诸如此类的一大堆符号 , 而是要知道在推导思想方面,数学的方法是什么,是用什么方法去培养的 , 借此训练学生主动思考。因此,虽然有的数学,比如平面几何,其中比较繁复的定理大部分在近代科学里没有用了 , 但是,对学生来说,平面几何是很好的逻辑训练 , 所以还是要学。美国教育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十分鼓励学生讨论。学生之间的讨论往往能够互相启发。因此,希望学校不要制造太大的考试压力 , 以便学生能够尽量发展自己。
其次 , 大学的数学教育要平衡发展。近代数学发展的结果,使得各种数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沟通也越来越多。因此,学生对所有不同数学的知识应有基本的了解。目前在国际上能够称得上好的数学家,至少都懂得两种不同的数学。比如读几何学的人,好多都懂得拓扑学上的理论或微分方程上的理论。如果只懂其中一种而不懂其它,以后会产生极大的弊病。
第三,要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多读参考书,多做研究。这与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讨论一样,都是值得提倡的。
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大学教师在指导学生时,不要太过强调一些抽象性名词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只是数学的语言,不是目的。数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数字,是几何的形象,是函数上的构造,是概率上的分布,等等,而它们和抽象的语言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上文为1980年12月1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的演讲节选)
数理与人文
我遇见过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他们对文艺都有涉猎。他们文笔流畅,甚至可以与文学家媲美。其实,文艺能够陶冶性情,文艺创作与科学创作的方法实有共通的地方。
好的数学家最好有人文的训练,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来将我们的科学和数学完美化,而不是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只跟着前人的著作做少量的改进,就以为自己是一位大学者。
中国数学家太注重应用,不在乎数学严格的推导,更不在乎数学的完美化。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数学家实在无法跟文艺复兴的数学家相比。
有清一代,数学更是不行,没有原创性!可能是受到乾嘉考据的影响,好的数学家大多跑去考证《九章算术》和唐宋的数学著作,不做原创性的工作,和同一个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英国、德法、法国的学者不断的尝试的态度迥异。找寻原创性的数学思想影响了牛顿力学,因此引发了多次工业革命。
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还是比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的修养还是不够,对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够丰富!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文学家说,其实是共通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有深度的民族,上述诗人、小说家的作品,比诸全世界,都不遑多让!
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不大注重人文修养,我们管理教育的官员们却有很奇怪的教育政策,他们大概认为语文和历史的教育并不重要,用一些浅显而没有深度的通识教育来代替这些重要的学问,大概是他们以为国外注重通识教育的缘故吧。但这是舍本逐末。坦白说,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有水准的国家和城市不反反复复地去教导国民们本国或本地的历史的。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一个小镇读书。他们在小学,在中学,将美国三百年的事情念得滚瓜烂熟!因为这是美国文化的基础。
我敢说,不懂或是不熟习历史的国民,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一代。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的根基比较浅,容易受人愚弄和误导。这是因为他们看不清楚现在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古代伟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下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为他们的子孙走错的路而感叹!中国五千年丰富的文化使我们充满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或许有人说,自己不想做大科学家,所以不用走我所说的道路。其实,它们并不矛盾。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再去学习任何学问都会轻而易举!至于数学和语文并重,则是先进国家,如美国等一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比较好的大学录取学生时都看SA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成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的就是语文和数学。
除了考试,美国好的中学也鼓励孩子多元化,尽量涉猎包括人文和数理的科目。美国有很多高质量的科普杂志,销量往往都在百万册以上。而中国好的科普读物不多,销量也少得可怜,从这点就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希望我们能渐渐改进!
最后要指出,数理人文和所谓博雅教育有莫大关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Willian C. Kirby,1950—)在2006年的周年通讯中说:“让我重申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博雅教育的目标广阔,既着眼于基础知识,鉴古知今,推理分析,又能培养学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兼且对科学的概念和实验的精准性有所了解,同时也强调因材施教,反对重覆不断的操练,顶住了过早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潮流。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是好些名校的优良传统,但这绝非哈佛大学的使命。我们希望哈佛学子在专注于某门学问的同时,成为一个事事关心、善于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人,毕业后矢志贡献于社会,并终身学习。”
台积电前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对上述看法甚为赞同。他说:“博雅教育启发我的兴趣,充实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曾说过,如果没有《红楼梦》、莎士比亚、贝多芬等等,我的生命会缺少一块。对我的工作而言,博雅教育提升我独立判断的思考能力,让我从工程师、工程经理、总经理、执行长到董事长一路走来,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受益良多。”
美国名校的教育使得不少的学者跨越不同的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有些学生在本科时读英文系,毕业后却可以成功创立高科技公司。当代在数学和物理上有杰出成就的威腾(Edward Witten,1951—)教授在本科时念历史。这些例子在美国名校不胜枚举,但在华人社会却不多见。这应当是美国倡导博雅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倡导数理人文并重的结果。
中国的教育始终走不出科举的阴影,以考试取士,系统化的出题目。学生们对学问的兴趣,集中在解题上,科研的精神仍是学徒制,很难看到寻找真理的乐趣。西方博雅教育的精神确实能增广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的热情,更能够培养大学问。举例来说,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可以说是于学无所不窥! 连我前年写的一本叫做《大宇之形》(The shape of Iner Space)的科普书,物理系有些教授也用来做为通识课本。多读多看课本以外的书,对我们做学问,做人处世都会有大帮助!
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生生不息,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表现出来。激情处,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至于万古长存,不朽不灭!伟大的科学家不也同样要找到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吗?
(本文节选自《我的教育观》一书)
作者简介: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71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33岁时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
丘成桐目前致力于为“数学强国”做贡献、带新人,他现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数学学科的发展和数学人才的培养。
编辑: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