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伯特兰·罗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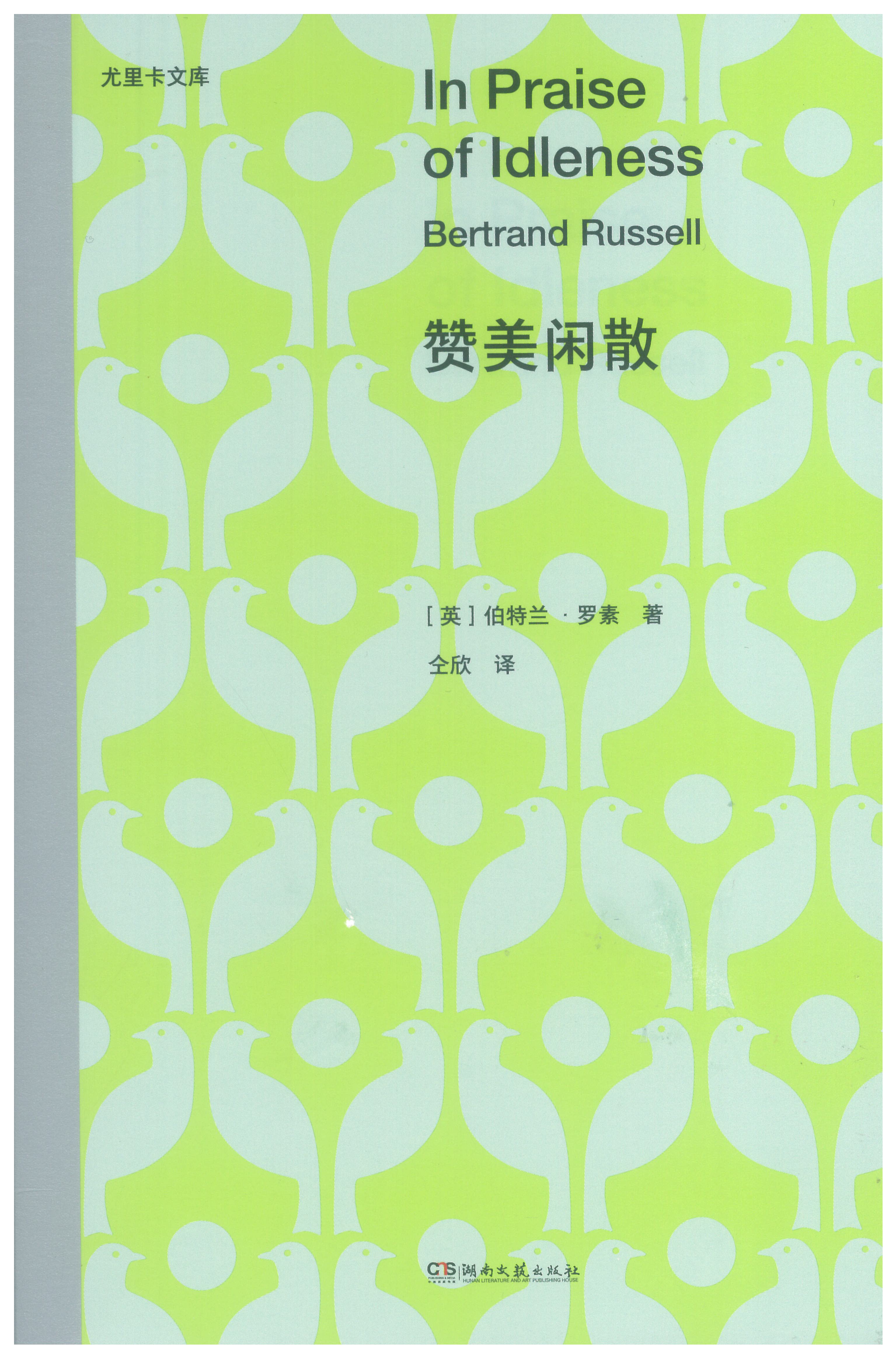
同我这代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这样的谚语长大的。
作为品行端正的好孩子,我对这类教诲深信不疑,并以此约束自我,努力工作至今。不过,虽然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观点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工作得过于辛苦,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现代工业化国家需要弘扬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理念。
大家都听说过那不勒斯旅行者的故事:旅行者看到十二个乞丐躺在地上晒太阳(故事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前),说会赏给最懒的那个一里拉。十一个乞丐都跳起来说该给自己,于是旅行者将钱给了第十二个乞丐。显然,旅行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对于享受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来说,想要真正做到闲散可谓难上加难,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宣传加以引导。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过下面的文字,能够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学会闲散,如此我便也没有白活于世。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工作的起源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要么是改变地面或其附近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要么就是吩咐别人去做。第一种工作辛苦且报酬微薄;第二种工作舒适且报酬丰厚。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既包括发号施令的人,也包括为发出何种号令出谋划策的人。通常,两个有组织的团体会同时提出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需要的不是有关建议本身的渊博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演讲和文字去说服别人,即营销的艺术。
在欧洲还存在第三类人(但美国没有),他们比从事以上两种工作的人更受尊敬。这类人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租金,这样其他人才拥有生存和工作的资格。这些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似乎应该赢得赞美。不幸的是,他们的游手好闲建立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他们好吃懒做的欲望,促成了人类辛勤工作的信念。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别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前,一个人的辛劳所得,通常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即便妻子同他一样卖力工作,即便孩子稍大一点也会加入劳动。基本所需之外的少量盈余没有给到生产者,而是被武士和神职人员霸占了。遇上饥荒,明明没有任何盈余,武士和神职人员却依旧像平日一样索取,以致无数劳动者贫困交加而死。这一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1917 年,许多东方国家至今仍在沿用。英国虽然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依旧盛行,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掌权才画上句号。在美国,这种制度在独立战争后便结束了,但南方除外,在那里,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个如此旷日持久又刚刚终结的制度,自然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理所当然想要工作的愿望,大都源于这一制度,但工业社会前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它不再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一种可以在整个社会进行平均分配的权利。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很明显,在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农民如果有选择权,便不可能将微薄的物质盈余拱手交给武士和神职人员,而只会减少生产或消耗更多。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被强迫劳动并上交盈余,但渐渐地,有人发现,可以诱导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观念会让他们认为拼命劳动是一种义务,即便生产所得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其他人闲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此前劳动中的强迫成分,管理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高于普通劳动者,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英国工薪阶层依旧会感到难以置信。从历史的角度看,“义务”这一概念向来都是权力阶层诱导他人为主人而非自己谋利的手段。当然,对此权力阶层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确有其合理性,比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时光,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绝对公正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下,公正地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劳动量,是可能得到大规模缩减的,大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军队里的男人、参与军需生产的民众,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战争宣传以及在战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从原本的生产岗位抽调来的。尽管如此,协约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
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掩盖了:借贷令民众误以为他们正在用未来养活现在,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画饼并不能充饥。大战充分证明了,通过对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现代社会只需一小部分劳动力,便可以令全体民众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如果大战结束时,那些原本为抽调民众参战或从事军需生产而创建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延续下去,并由此将工作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旧制度卷土重来,受雇的劳动者要被迫工作更长时间,而其他人则沦为忍饥挨饿的失业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依据的不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其表现出来的勤劳美德。
工作是义务,但也仅限于平衡食宿消耗
这便是奴隶制国家倡导的道德,可当今世界的外部环境已经同奴隶制时期截然不同,难怪这种道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一定数量的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别针生产。他们每天工作(比如)八小时,生产的别针刚好能满足社会需求。这时,有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同样数量的人生产出的别针由此翻了一倍,但世界消耗不掉这么多别针:别针已经很便宜了,再降价也不可能卖出更多。在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所有参与别针生产的人会将工作时间由此前的八小时缩短为四小时,这样一切便可以保持正常的运转。但在现实世界,人们却认为这是意志消沉的体现,于是继续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导致别针生产过量,一些雇主走向破产,一半参与别针生产的人迎来失业。从最终结果看,社会整体的空闲时间同四小时工作制一样,只不过现在一半人无事可做,另一半人劳动过量,不可避免的闲暇沦为普遍苦难,而非普遍幸福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吗?
穷人应当拥有闲暇的观点一直令富人感到不可思议。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是正常现象。儿童有时也要工作这么久,至少每天十二小时是常态。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反驳说,工作使得成年人免于酗酒,儿童无暇捣乱。记得在我小时候,工人刚刚获得投票权后不久,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共假期,上流社会对此极为不满。我记得当时一位老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干什么?他们就该工作。”现在的人自然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但这种观念依旧存在,而且是造成众多经济乱象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抛开迷信,坦诚地讨论一下工作的道德。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成果。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总体来说不令人愉悦,那么,一个人的消耗超出产出便是不公正的。当然,他的贡献也可以是某种服务而非商品,比如他是医护人员,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做出一定贡献,用以平衡自己的食宿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确是每个人的义务,但义务也就仅限于这个程度了。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甚至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劳动都无须履行,比如继承大量财富或嫁入豪门的人,对此我不打算详谈。我不认为一些人能够游手好闲的事实,对社会的危害能同让劳动者不是过度工作就是忍饥挨饿相提并论。
假设社会采用某种适度、理性的管理模式,普通劳动者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社会所需,还不会造成其他人失业。这个观点令富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在美国,即便是富人也常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听到有人主张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闲暇,这些人自然会感到愤慨,除非是将闲暇当作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事实上,他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闲着。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希望儿子拼命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文明人,却又一点都不介意妻女无所事事。在贵族社会,对悠闲自得近乎势利的羡慕,男女都会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却只限女性,但这并不表明如今的现象更符合逻辑。
生活的乐趣,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大多数人享受闲暇的权利,只有替别人受苦的愚蠢的禁欲主义在让人们坚持过度工作,虽然当初工作的需求早已不复存在。
在支配俄国统治的新信条中,虽然很多都与西方传统教义大相径庭,但一些观念还是坚固如初。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宣传的人,只要提到劳动的尊严,就和世上其他那些宣扬“诚实的穷人”的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勤劳、节制、为长远利益努力工作,甚至是服从权威,所有这些信条再次浮出水面。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有一些共通之处。长久以来,男人都承认女性圣洁的高贵,通过强调圣洁比权力更重要,来掩饰女性地位的低下。
女权主义者最终认定,她们既要圣洁也要权力,因为她们中的领袖人物愿意相信男性对女性美德的吹捧,却不接受男人所说的政治权力无用论。在俄国,体力劳动者的经历也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和他们的奉承者都在大书特书“诚实劳动”的概念,赞美简单质朴的生活,宣扬穷人比富人更可能上天堂,试图让劳苦大众相信,改变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工作尤为高尚,就像男人试图让女人相信她们从性奴役中获得了某种特殊的高贵。在俄国,一切对体力劳动的赞美都备受重视,以至于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不过,从本质上说,呼吁恢复这一信条的目的和此前不同:它是为了让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投身于某些特殊任务。劳动者被塑造成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根基。
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可能确有可取之处。一个自然资源丰饶又不太可能依赖信贷的大国迫切需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必不可少,甚至可能会带来巨大回报。可是,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无须长久劳作便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西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然无意实现经济公正,大部分生产总量便落到了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无须从事任何劳动。由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国家统一调控,一大堆压根儿就不需要的东西被生产了出来。我们让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另一部分人超负荷工作。如果这些方法均效果不佳,我们就制造战争:像刚刚接触爆竹的孩子,我们安排一些人生产烈性炸药,再安排另一些人将其引爆。通过将所有这些手段相结合,我们终于维护住了普通民众唯有终日辛劳的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辛。
在俄国,由于经济相对公正,生产集中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一旦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且让全民实现基本的舒适,就开始逐步缩减工作时间,并在各个阶段召集民众投票,让大众决定是要更多的休息还是更多的商品。不过,既然宣扬了辛勤工作是至高美德,政府便很难致力于打造一个让人们多休闲少工作的人间天堂。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不断找到新方法,牺牲当下的闲暇以提升未来的生产。
我最近读到,俄国工程师提出一个巧妙的方案,通过在喀拉海峡建造堤坝,提升白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这个计划的确令人敬佩,只不过,北冰洋的冰天雪地虽能彰显劳动的可贵,却将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推迟了整整一代人。这类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能意味着人们在为了辛劳而辛劳,而非通过辛劳这一手段,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改变物体位置的工作虽然对生存来说必不可少,却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筑路工的地位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是被两个因素误导了:第一便是让穷人感到满足的必要性,这让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在宣扬劳动的尊严,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处在“不体面”的生活状态;第二便是机械装置带来的新乐趣,让我们不禁为能在地球上实现如此惊人巧妙的变革感到愉悦。
不过,这两个动机对实际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如果你问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回答:“我热爱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让我觉得我是在完成人类最崇高的使命,我也乐于想象人类能为地球家园带来的巨大改变。没错,我的身体需要定期休息,我也会尽可能满足它的需求,但要说最开心的,那无疑还是清晨到来,再次回到繁重却令人无比满足的劳动中去。”我从未听过哪个劳动者说过这种话。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他们享受的无论是何种乐趣,都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缩减工时之后呢?
有人又要说了,少量闲暇固然令人愉快,但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工作四小时,人们肯定又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了。如果说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竟会显得合情合理,只能说明我们在谴责人类文明。
换作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这种观点都不正确。以前人们都知道如何轻松自在地生活,可这种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抑制了。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都应当另有目的,却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
比如,严肃认真的人一直在批评泡电影院的人,说看电影会诱导年轻人犯罪;可他们又认为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令人尊敬,因为那是工作,会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只有能带来利润的活动才值得认可,这种观念无疑打乱了一切。卖肉的屠夫和提供面包的师傅都值得赞美,因为他们在赚钱,但享受他们提供的美食却是不务正业,除非吃东西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儿。
概括来说,人们认为赚钱是好事,花钱是坏事,这一观点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它们明明只是构成交易的两个要素。这就如同在说,钥匙是好东西锁孔却是坏的一样。劳动产品的价值,只能依据它们被消耗后产生的价值来衡量。社会中的个人为利润工作,但其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耗他所生产的东西。在这个辛苦劳动只为赚钱的世界上,个人同生产的社会目的的分离,使人们无法清晰地思考。对生产考虑过多,却很少考虑消费,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我们完全无视了享受和简单的幸福,也不以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快乐来评定生产的价值。
建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四小时,并不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必须浪费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上。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应该有权获得生活所需以及基本舒适的生活状态,其余时间可依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对任何社会制度来说,将教育向前推进都至关重要,而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人们的品位,让他们能够更加明智地利用闲暇。我想说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所谓的“高雅”爱好。除了偏远的农村,现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乡村舞蹈了,但当初创造这种舞蹈的冲动,却一定还保存在人类的天性之中。现在,都市人的乐趣越来越被动:去影院、看球赛、听广播等,因为能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精力早已被工作消耗掉了。如果能再多一些闲暇,他们一定会再次主动创造消遣并乐在其中。
在过去,有闲阶级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民众都属于劳动阶级。虽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言,但有闲阶级享受了种种好处,因此必然会成为压迫者,缺乏同情心,并开始发明理论来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权辩护。这些事实令有闲阶级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尽管存在这般缺陷,他们却几乎贡献了人类的全部文明。他们培养艺术、发现科学、著书立说、创造哲学、完善社会关系,甚至连被压迫者的解放,往往也得益于这些贡献。离开有闲阶级,人类便无法走出野蛮。
可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却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个阶级的人从未被教导过勤奋,作为整体来看智力水平也相当一般。这个阶级或许会贡献出一个达尔文,但与此同时又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乡村绅士,除了狩猎和惩罚偷猎者,他们从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尾声
如今,大学以相对系统的方式,旨在为社会贡献之前有闲阶级出于意外或是作为副产品提供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欠缺。大学生活同外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人,往往不了解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和问题。不仅如此,学术界常用的表达方式,还常常令他们的见解无法发挥出对民众应有的影响力。另一个缺陷是,大学教育过于按部就班,在意独创性研究的人可能会举步维艰。因此,当学术高墙之外的所有人都忙碌到无暇关注任何非功利性事务时,学术机构虽然有用,却承担不起守护文明的重任。
在一个没人会被迫每日工作超过四小时的世界里,每一个对科学怀有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每一个画家,无论作品好坏,都可以专注于绘画而不用担心挨饿;年轻作家无须为吸引眼球去创作粗制滥造的作品,想着先获取足够的经济支撑再去创作不朽名篇,毕竟经济独立后,他们往往也丧失了品位和能力;那些从事具体专业工作的人,只要对经济或政府事务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就可以投身其中,而不必成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与世隔绝正是大学的经济学家脱离现实的原因;医务人员将会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医学的发展,教师们也不必气急败坏地套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学生自己年轻时学到的知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知识可能已经不再正确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再被精神紧张、身心疲惫和消化不良困扰。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会令闲暇更显愉悦,却不会造成疲惫。休息时间不疲惫,人们便不会只追求被动乏味的娱乐,一百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愿将工作之余的时间投入对公共有益的事务,而且,由于不需要以此为生,他们的独创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不必去迎合老学究定下的标准。
不过,闲暇的益处并不局限于这些特殊情况。世间的平凡男女,如果有机会过上幸福生活,必将会更加与人为善,更少迫害和猜忌他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战争,更何况战争还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工作得更久更辛苦。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天性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但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现代生产方式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拥有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们却选择了让一些人劳碌致死,另一些人忍饥挨饿。迄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机器诞生前的那股忙碌劲儿,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摘编自《赞美闲散》,较原文有小幅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编辑: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