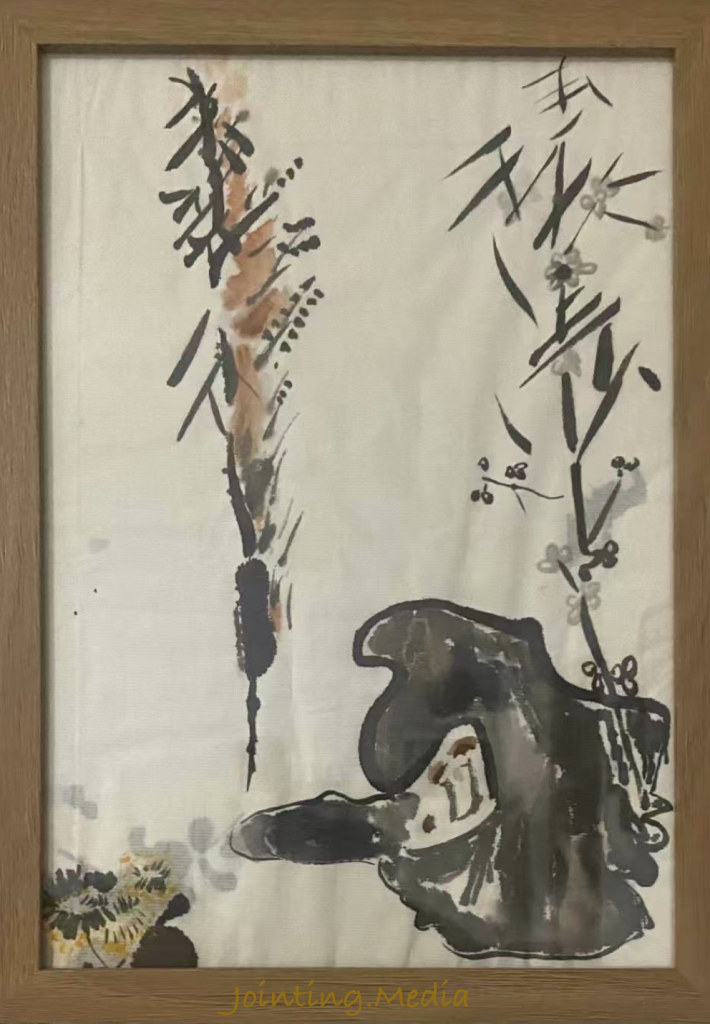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陈娅 , 武汉, 2025-08-24
援笔启思,思以致远
两位拥有高学历的中国成年女性,在繁华都市中的出租屋内饿死——这并非虚构情节,而是分别真实发生在2023年日本东京与2024年中国陕西咸阳的事件。
与许多人一样,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质疑其真实性;经查证后,却在错愕之余更感唏嘘。网络上有诸多流传播散,却鲜有人深入剖析她们心理状态的演变过程,或其与家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导致她们心理困境的具体成因已难以追溯,笔者仍希望尝试略作探析,以期从中获得某些反思,在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过程中,能与自己和解;在教育未成年的孩子的过程中,能好好引导他们,建立健康的心理体系,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从共性来看,这两位中年女性都未能实现理想的生活——一位离乡背井,执着地试图融入理想的异国环境;另一位则多年持续报考公务员却始终未能“上岸”。她们同样缺乏积极谋生的意愿,导致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同样与家庭切断了联系。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二人都属于慢性自杀。她们并非单纯“饿死”,而是在与“意义的虚无”进行一场绝望的抗争之后,选择了“自我删除”。
一、“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y)的视角
两位高学历女性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环境中“饿死”的悲剧,从表面看,违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优先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原则。
马斯洛理论常被误解为必须100%满足低层需求才会产生高层需求。但马斯洛本人认为,这种顺序并非绝对。大多数人各层次需求是部分满足和部分未满足并存,并会相互交织影响。对于许多高度理想化、追求精神价值或存在强烈荣誉感的人而言,高层次需求(如尊严、自我实现)的严重受挫,确实可能压倒其对基本生存需求的渴望。历史上的一些绝食抗议者或“不食周粟”的典故,也体现了在特定情况下,人对信念和尊严的追求可以超越生存本能。
马斯洛在后期理论中提到,当一个人高层次需求(如自我实现)受挫,尤其是存在主义价值(如真理、美、正义、意义感)缺失时,也可能引发一种严重的心理病态,他称之为“超越性病态”。
这两位女性的选择并非简单地“违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是悲剧性地演示了当高层次的需求(如爱、尊重、自我实现)被极度扭曲、挫败,并与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病态地捆绑时,如何可能压倒甚至摧毁了对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渴望。它更多地揭示了在特定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人心理特质下,追求卓越的动机如何可能异化为自我毁灭的驱动。
因为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复杂且深受心理和环境影响。健康的自我实现,应建立在对自我价值的无条件认可(即使遭遇失败)和现实的支持性关系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僵化、狭隘且充满压迫性的“成功”定义之上。
“完美主义”与“病耻感”的绞索
对于许多从底层通过教育打拼上来的孩子,“成功”不仅是个人追求,更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期望甚至解脱的希望。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家庭期望。这种压力可能转化为极端的完美主义。她们将自我价值完全绑定于“成功”这一结果。一旦受挫,强烈的“耻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耻辱、失败的符号)会吞噬一切。咸阳女子的父亲按其当地风俗未让女儿骨灰入祖坟,这或许也反映了某种社会文化压力。这种“无归”的恐惧与羞耻,可能比饥饿更难以承受。
“关系创伤”与“自我惩罚”的绝境
自我的“消失”或许是对内在批判声音的最后屈服。她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的关系模式中(可能源于家庭或社会比较)。当无法达成目标时,她们内心可能有一个严苛的“批判者”不断重复“你毫无价值”、“你不配吃饭”、“你让所有人失望”。于是,“不再消耗资源”的自我惩罚,乃至自我删除,就成了这个内在批判声音的终极执行。“饿死”成为一种被动且彻底的自我否定方式。
“理想化”与“现实感脱节”的囚笼
东京女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极端认同和对现实的否定本身也是一种脱离现实、沉浸于理想化世界的表现。当一个人将全部精神寄托于一个极度理想化且脱离现实的目标(无论是“绝对公平”、“纯粹的成功”还是“完美的彼岸”),而现实又不断给予打击时,可能导致严重的认知失调。为了维持心理上的一致性,个体可能会选择否定现实(包括自身的生理需求),最终被困在自我构建的囚笼里,无法对外求援或采取现实的生存策略。
这两位女性对“成功”和“意义”的理解可能非常狭隘和僵化。例如只有“考上公”或“在国外出人头地”才叫成功。当这个唯一的、被极度理想化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她们可能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存在主义绝望和价值观崩溃之中,觉得“一切都完了”。这种意义的彻底丧失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超生理饥饿的痛苦,使得维持生存变得无关紧要。
二、虚无主义的深渊vs存在主义的重压
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虚无主义(Nihilism)的哲学视角看,她们的行为是当“存在”本身的重压与“意义”的彻底真空相结合时,一个个体可能做出的终极反应。
虚无主义并非主动选择“无意义”,而是发现所有预设意义都不可靠后的一种幻灭状态。
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都遵循着一个清晰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意义公式”:
寒窗苦读 → 金榜题名 → 获得体面工作 → 实现价值/光宗耀祖。
这个公式是她们对抗虚无的铠甲。然而,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个公式:咸阳女子的公式在“获得体面工作”这一步卡死了。多次考公面试失败,证明了她无法兑现“意义公式”所承诺的回报;东京女子的公式更复杂,加入了“逃离”与“投机”(赴日、炒币),但同样彻底失败。
于是,意义的彻底瓦解。她们陷入了消极虚无主义的深渊:如果遵循规则、努力奋斗都无法换来意义,那么一切是否本就是徒劳?“学霸”身份这个曾经的核心价值,在现实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反而成为一种反讽。
饥饿感是身体最原始的呼唤,是生命寻求延续的信号。但当一个人判定生命本身已无价值时,这种生理信号就被切断了。进食这个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意义——“我要继续活下去”。而当“活下去”的理由消失时,进食也变得毫无意义。“饿死”于是成为一种逻辑终点:既然生命无意义,那么维持生命的活动也应停止。 这是一种将哲学层面的虚无最终转化为生理现实的极端行为,是“虚无”的生理化。
存在主义承认世界的荒谬与无意义,但其核心是一种激昂的号召:即使如此,你也要亲手创造意义! 而这,恰恰是两位女性无法承受之重。
你没有什么“学霸”或“成功者”的预设本质,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谁。对她们而言,这是最恐怖的真相。她们前半生都在努力符合一个“本质”(好学生、成功者),却突然发现这个“本质”是虚幻的。她们被抛入一种绝对的自由中:你现在可以选择成为任何⼈,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一个回老家的“失败者”。但这种自由没有带来解放,反而带来了存在性焦虑(Angst)。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感到的眩晕,这不是害怕坠落,而是害怕自己会跳下去的自由。她们害怕的,正是“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失败者” 的这个可怕自由。
哲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和萨特都论述过,巨大的自由令人恐惧,许多人会选择 “逃避自由”。咸阳女子反复考公,本质上是在逃避选择另一种生活的自由。她宁愿死死抓住旧公式的残骸,也不愿面对“定义新自我”的自由和责任。东京女子投身于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自由”上交,让一种新的绝对信条来告诉她自己是谁,从而逃避自我选择的痛苦。
萨特将这种逃避称为“自欺”(Bad Faith)——欺骗自己,说自己没有自由,必须活在他人的期望中。但当“自欺”都难以为继时(考试彻底失败、投机彻底破产),她们就直面了那个赤裸裸的、毫无借口的存在本身,最终被压垮。
存在主义的创造意义,要求个体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一种深刻的孤独。你的意义,无人能替你证明和承担。两位女性切断了所有社会联系(拉黑家人、断绝往来),这既是虚无主义下的退缩,也是存在主义层面上的:他们拒绝再扮演任何角色(女儿、精英),也拒绝承担为自身存在创造意义的绝对责任。 在这种极端的孤独中,“自我删除”成了最终的解脱——不再是“我选择成为什么”,而是“我选择不再成为”。
从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视角看,这两起悲剧的深层逻辑是:虚无主义为她们拆解了旧世界,让她们看到曾经赖以生存的意义是虚假的,使她们陷入“为何而活”的虚空;存在主义则向她们展示了构建新世界的可怕自由与重担,而她们在目睹旧世界的废墟后,已无勇气和力量再去亲手建造。
于是,“饿死”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行动。它是一种对虚假意义的最终拒绝(我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是一种对自由重担的彻底放弃(我也不必再选择如何活了)。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终极的“非选择”,是灵魂在意义真空中停止呼吸后,身体所做出的最终呼应。
三、与自我和解,拉紧生命之弦
笔者认同“人生本无固有意义”的观点,认为生命实质上是一个自我定义、主动寻求并赋予意义的过程。
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两位盲人以说唱为生,心中始终怀着一个信念:当弹断一千根琴弦时,便能取得药方,重见光明。然而当老瞎子真正弹断一千根琴弦后,却发现所谓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希望彻底破灭,“他的心弦断了”;他意识到那追寻一生的目的竟是虚无。他在药店门前枯坐数日,于小旅馆中久久徘徊,待耗尽所有积蓄后,想起了自己的徒弟——那个并不热爱说书、一心渴望去看世界的年轻人。师父辗转寻回徒弟,当被问及是否吃下秘方的药时,他说:“我记错了,不是一千根,是一千两百根”。自知余生无多,他嘱咐徒弟继续弹琴说书,并将新的“秘方”封入徒弟的琴槽。就在这时,老瞎子猛然醒悟,记起师公临终之言——“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并再次对徒弟说道:“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就够了”。
“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就够了”。遗憾的是,前文提及的两位女性,未能拉紧生命的琴弦,也似乎无人为她们封存一份继续前行所需的“秘方”。尽管她们的情况属于极端个案,但现实中亦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例如那位边做快递员边备考,最终赴港读博的女性;或从民办二本毕业,通过担任北大保安并十年备刻苦读,最终通过法考成为律师的人……这些积极求索的案例虽亦属个别,却无疑更为普遍。
不可否认,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许多人面临减薪、失去曾经的高薪体面工作,或长期待业在家等困境,甚至有人选择结束生命(如上海金融业女性或某大厂高级工程师的案例)。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直面挑战,例如从脑力劳动者转型为体力劳动者,以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当外在的标签、社会的公式被剥离后,我们是否拥有为自己生命亲手创造并坚守意义的勇气?我们构建的“意义”大厦,是否能经得起幻灭的风暴?
插图:陈娅习作(2022)